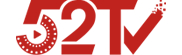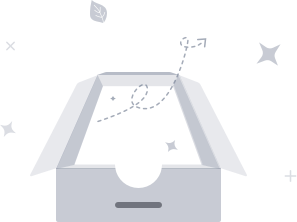死亡中诞生爱的秩序:《破·地狱》及其“止血”“催泪”的情感技术
由陈茂贤执导、上映于2024年末的电影《破·地狱》,凭借对丧葬仪式的传统再现,家庭、性别、生育等时下伦理困境的全景式扫描,以及讲述者自身舒缓稳健的叙事节奏,在香港票房登顶,迅速摘得了“华语电影票房冠军”的惊人成绩。影片中,婚礼策划师道生由于债台高筑,经亲友介绍转业为丧仪经纪人,他不仅与喃呒师傅文哥成为了搭档,也逐渐深入其心乱如麻的家庭生活。二人由针锋相对的冤家,逐渐变作彼此生命重要的见证人、料理人、引路人,简洁易懂的脉络之下,指向的实则为由道生代表的年轻一代对于生死伦常持有的哀悼观,与年长如文哥的父辈之间发生的断裂与碰撞、差异与交融。轮舞般的双视角呈现方式,编织出了故事质地的丰富褶皱。对于各执一词的双方,电影镜头始终俯之以耐心的倾听,尽量公允地还原了不同人群面临的生活难度,凭借视角的包容性,不断荡开话题讨论的空间,也令略显古旧的题材焕然一新,顺着婀娜轻盈的南音小调,一路延展至西装革履、大厦环绕的当代生活。

《破·地狱》海报
其中,支持并助推着人物自然变化、使各种观念柔软如海绵一样充满了伸缩力与可塑性的,是电影对于“身体”的精彩调遣。实际上,身体不仅占据了绝大部分银幕的前景,而且已经深度参与叙事进程之中:作为殡葬业的“目标客户”,一具新身体的出现将为人物刷新任务命题;如何“超度”这些或鲜活或停止了呼吸的身体,则事关清理它们尚粘附着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与情感纽带;当它出现,联合面孔、眼泪、气味等众多形式,就此成为了一门比一般语言“更含混也更忠诚的语言”,这意味着身体正在以其独特的句法尝试沟通并提醒人们重新掌握它——毕竟,没有任何一种对死亡的解释比一副遗体更具权威性,那么为了处理它们,释放情感、直面丧失的“哀悼练习”成为必要。本文意在从《破·地狱》的身体视角出发,通过四次殡葬过程探讨道生、文哥代表的两种仪式观念曾如何争夺对死亡的解释权,而随着故事推进,昔日的矛盾被证明为莫须有,又最终反过来为形形色色的身体所包容。第二部分则着眼于死亡面向生者授予的“哀悼练习”,即哀悼是如何呼唤死者与生者的同时在场,并在二者的面孔交织之中完成自身。第三部分则试图证明,如果哀悼死亡包含了“释放情感”“直面丧失”两种关键环节,那么影片对喃呒师女儿文玥无意间的塑造,恰恰透露出了女性多血、多泪的身体内部天然蕴含的哀悼经验。
一、超度“死者”还是“生者”?——仪式观念与情感经济
喃呒师文哥的家族世代以入殓为业,到这一辈早已对传统丧仪的衣冠、形制、阵势了然于心,甚至“传男不传女”的规矩也从未打破——“老祖宗定下的规矩”是他时刻提起的口头禅,为了维护它们,他严厉地拒斥所有不合礼数的决议,连儿女也不例外,俨然一副忠诚的卫道士形象。与此同时,秉持“微笑服务”的道生比照起来显然要亲切、讨喜得多,这一点实则离不开他昔日作为婚礼策划的职业习惯。道生巧妙地将“私人订制”的运营模式移挪了过来,仪式流程、棺椁材质乃至纪念品的一切需求皆以客户为先。这种理念不仅在替一位母亲花重金保存儿子尸体一事上初见成效,也很快凭借一种令人熟悉的“进步性”赢得了观众的认同。
之所以感到似曾相识,是因为“超度生者”的仪式观脱胎于今日的“情感资本主义”时代,在强调情绪价值的社会气氛中,情感正进一步成为虚拟货币,被纳入金钱交换的逻辑范畴。如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通过航空公司对女空乘的情感培训察觉到,这种情感劳动“要求一个人为了保持恰当的表情而诱发或抑制自己的感受,以在他人身上产生适宜的心理状态——就空乘而言,就是要让乘客产生在一个欢乐又安全的地方得到关怀的感觉。这种劳动要求意识(mind)与感受(feeling)之间的相互协调,有时还要利用自我的某种来源,即我们视作自身个性的深层且必要的部分。”当商业行为接管了情感的信号功能,道生深谙整场交易环节中,家属不断放大的情绪将影响丧仪的选择,而这正是他主要的盈利来源,因此,当第一位客户表示只想一切“按照去世兄弟的心意操办,钱并不重要”之后,他便根据死者的生平细节,针对性地推销起抚恤家属的相关产品,并且也格外乐意承接甄小姐离奇却出价不菲的心愿。

《破·地狱》剧照
值得关注的是,影片借助道生的前后变化,呈现了情感经济的暧昧之处。一方面,它的出现具有生产性,当媒介兴起并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原子化时代,个人的主体性危机加剧,时刻承受着无法挽回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在身心施加的粉碎性力量,情感经济则关注到这一部分需求,它借由服务的形式,肯定和维护了人对存在的渴望。无论是引发笑料的汽车追悼会,破例带恋人进入入殓室,还是要求文玥主持“破地狱”为父亲上演最后一舞,道生始终感受和满足着客户层出不穷的想法,并不以此为麻烦,他出卖的实则是让任何人都能在自己面前“哭出来”的情感技术,而这些交易也由于身体的在场以及身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良性的情感互动。在片末,文哥承认“你教了我很多”,这也是情感经济及其在现代社会上演的“关系美学”带来的启发,即基于脆弱与变化衍生出的共识,更有利于人走出由电子楼群构筑的幽禁状态,在他者身上找到自我确认、自我实现的出口。
不过,影片在开头便借助明叔之口谈到了仪式的核心问题:“这件事是发死人财,不管做什么都要万事小心。”当情感经济介入丧葬行业,它受到商品买卖逻辑操控的部分,也为后者带来了危险。起初道生为了赚快钱入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出售服务,那么再温情的互动,也无法避免陷入“情感表演”的可能。他将殡葬服务按需分配,用金钱收买化妆师代劳,并为贵妇人打破行业规定,凡此种种,都将死后的生命再次拉入了活人的阶级世界。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从战争的讣闻对象中发现了一种“限制性的人类定义”:“支持维系生命的方式有所不同,在全球各地,身体脆弱特质的分布方式也大相径庭,有些人的生命受到严密保护,如果他们的神圣权利受到侵犯,就足以引发战争;其他人的生命则缺乏如此果断而坚定的支持,他们甚至是‘不值得哀悼’的生命。我们不难发现哀悼的等级差异。讣闻中就存在着这种等级分类:讣文迅速地整理总结生命,并为逝者赋予人性,这些人大多是已婚或已订婚的人、异性恋者、幸福的人、遵守一夫一妻制的人。但这只是一类经过筛选的‘生命’。”情感经济操纵之下的定制葬礼,同样源源不断地产生了被筛选的生命,这显然违背了平等的初衷,也残忍地剥夺了死者尊严。在这一角度上,“墨守成规”的传统仪式反而凭借森严而不可轻易更改的流程凌驾于金钱之上,使万物服膺于更高存在的力量,彼此之间价值均等,分享着同一份祝福和安宁。实际上,深受戈夫曼影响的社会学者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高度关注仪式情境下不断衍生的情感能量,他将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从彼此身体感受到的“微观节奏”视为仪式的核心:“当人们开始越来越密切关注其共同的行动、更知道彼此的所知所感,也更了解彼此的意识时,他们就会更强烈地体验到其共享的情感,如同这种情感已经开始主导他们的意识一样。”正如欢呼的人群加剧了兴奋,庄严的葬礼则使心灵更加哀伤,柯林斯承认这其中潜在着失败的可能性(并且,在他看来,流于空洞的仪式仅能被称作“正式”的),可这程序一旦成功,它召唤出的精神效力却也不容小觑,把主体间的短暂体验转化成了一种更稳定的情感,那就是“对于此时聚集起来的群体的依恋感”。概言之,虔信的保留有效弥补了资本逻辑中人存在的价值失落,二者和而不同,相依互融,得以在和平的磋商中维系情感活性。
二、“哀悼练习”:情感关系的丧失与修复
尸体不仅征服了两位丧仪师,令他们放下了各自的偏见,专注于合作完成对亡者最后的道别;同时,它们也最大程度地暴露在银幕上,几乎完全揭开了死亡的面纱,不再是一段轻描淡写的旁白,一帧转瞬即逝的蒙太奇,反而以最为腥臭、丑陋的面目零距离出现,力求真实和还原,邀请观众与剧中人物共同完成一场大型的“哀悼练习”。
有如丧母后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哀悼日记》中写下的那样:“以前,死亡是一个事件、一个突发状况,因此,会让人骚动、关切、紧张、痉挛、抽搐。突然有⼀天,它不再是事件,⽽是⼀种持续状态、沉甸甸、无意义、无以⾔宣、阴沉、求助无门:真正的丧伤无法以任何形式表述。”在巨大的丧失面前,语言是徒劳的,因此在更多情况下,电影选择用沉默的镜头对准那些业已掌握了终极秘密的人体,运用面孔、气味和不再完整的器官组织,将死亡还给肉身。这点在道生为丧子的母亲封存尸体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生动。当棺椁开启,母亲执意不肯火化的男童身体在数月的拉扯之下几无完形,顺着后背,令人作呕的乳白色液体伴随飞蝇汩汩渗出,而空荡的暗室瞬间被那肉眼可见的湿腐气充斥——光是特写细节就为视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遑论支离破碎的骨与肉,以及被毁灭的阴影笼罩着的面容。主持防腐工作的道生尽管全副武装,仍然难以接近这副停止运作的躯干,它意味着人的真正离去,器官衰竭,肌肉腐坏,毒气替代了均匀绵长的呼吸,恶臭威胁并破坏了一整套生命秩序,死人的身体由于这种全然的陌生性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他者,与活人的身体区别开来。

《破·地狱》剧照
在暴露生命终结的原始恐怖同时,对它的跨越也同步展开。一个细节是,影片中的每一位死者入殓时,都安排了其重要的关系人站在身旁,见证由生至死、又由毁坏至修复的过程。不舍儿子的母亲,不被承认的恋人,似乎需要清理的不仅是这些死者腐坏的肉身,还有他们身上粘附的亲密关系。在至亲之人的凝视下,入殓师启动工作,细致地调整死者的神情姿势,让他们穿上熟悉的衣服,面容恢复得与生前并无二致,仿佛只是睡去。这些镜头处理得极绵长,为了强调时间的存在——从眼前人逐渐膨胀起来的脸庞上,生者重新获得了对时间的感知,二者间的记忆正在流淌又即将停格,此时,死者的身体既是“拥有时间”的身体,也是“失去时间”的身体。关于失去,巴特勒如此描述道:“当我失去你,我会哀悼这失去,也会变得无法理解自身。没有你,我是谁?悲伤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政治社群的复杂。悲伤首先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同他人之间的关系纽带,这一纽带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相互依存状态与伦理责任。如果我的命运始终无法同你的命运分离,那么,这种关联就使我们紧密相依。”正如影片中的亲属们,在充满绝望的观看之外,他们还不约而同地伸出了双手:母亲抱住了尸水淋漓的儿子,女人亲吻了恋人的额头,用温暖的身体容纳了此时已经完全陌生的“他人”,似乎借助死亡,以及由死亡引发的“拥有”与“失去”之间的激辩,爱的秩序奇异地诞生了,它扎根于这根深蒂固的张力结构,扎根于绝对的陌生而非熟悉之中,并带来一股神圣的强度,它用这幅场景中生者与死者面孔的交织,在器械处理下不光是尸体、与之亲密的人同样得到了修复来证明,爱正在于有如入殓和哀悼般的时空同频。置身最后短暂的相处中,我们才真正地意识到彼此联结至深,并且(一个人代替另一个人)回过头,将这些同频时刻命名为永恒。
三、止血和催泪的技术:作为哀悼“元场所”的女性身体
虽然在勾勒文玥时,影片未能避免对女性的脸谱化想象,但它的笔力受限之处,却为延伸出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考潜质。根据上文解读,当故事专注于两位男主人公的交锋,以此来追问“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哀悼”时,一旁的文玥身上所流露出的性别气质,实则也在积极地回应这个问题。作为女性,她的生理特质曾一度受到诟病:沾有“经血”的衣物会冲撞老祖宗的衣袍,滚烫的“眼泪”不宜粘在遗体上——这些针对女性身体的行规不仅断送了文玥的梦想,也致使她成为急救员之后,仍然在为这副面对死亡时无法理性的身体而终日自责。

《破·地狱》剧照
然而,诸种现实状况表明,多血多泪的女性身体为文玥带来了丰富的止血和感知疼痛的能力。“月经”是规律性造访女性体内的流血事件,它的痛苦无法言说,更难以从源头上予以避免。每逢经血不期而至,她们必须一次次地接纳疼痛,学会消化它们,每日清洗遗留在衣物上的分泌物。长期磨合下,女性自然会提高身体疼痛的敏锐度,以及对于“看不见的痛苦”的想象力。作为救护员,死亡同样近似于一次“疼痛的造访”,周而复始地对文玥的身体形成伤害。因此,当男同事揶揄她“经历这么多次,应该习惯了吧”时,文玥本能地感到了愤怒,并毫不留情地回应道“怎么可能会习惯”,此处便较为明显地呈现了两种思维的区别。当前者用工具理性隔绝死亡时,疼痛却赋予了文玥一种优美的伦理,那就是对每一次受伤都保持震惊。因死者而感受到的难以磨灭的遗憾,转化为急救时全力以赴的动力,无论是为邻居老人免费做体检,还是心肺复苏时专业而强劲的姿势,女性成长历程中反复承受的流血经验,最终熔炼为了一种止血能力。除此以外,血的到来也改造了女性对“污秽”的认识。由于代谢频繁,她们需要加倍关注生理卫生,保持身体清爽干净,从自身上积累的照护经验,也在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中发挥效用。电影中,随着哥哥的远走高飞,文玥咬牙接过了料理失能老人的责任。面对曾指责自己“脏污”的父亲,她无微不至地为其更衣洗漱,处理老人的排泄物,很快适应了照顾者的角色。这得心应手的照护能力,正是女性身体赠予世界的礼物。
感受之后,如何对当下的情感进行描述,在普遍沉默压抑的谈话氛围里,文玥的嬉笑怒骂也显得格外醒目。入殓师中有一条特别的行规,即亲人不要将眼泪滴在尸体上,否则亡灵将难以获得宁静,在泉下“安息”——在这种语境下,因强烈情感而流出的热泪,顿时成为了动摇人心之物,它的出现由此变得恐怖,具有破坏性。反之,“不流泪”则发展为一种新的职业理性,不断监控、规训着人的身体,使它们仪表得当,不至过分哀戚。谨遵祖训的文哥就拥有一具从不流露真情的身体,道生注意到他“只在儿女不在眼前时,才能轻松地表达感情”,不仅自我克制,也无法接受他人的情感输出,无论文玥带着愤怒斥责,还是满怀柔情地询问,他都沉默以对,强行中断直接的情感交流。尽管临别前,这位父亲终于有勇气以遗书的形式剖白内心,承认了自己对子女的爱与愧疚,但仍然无法弥补多年家庭生活中,情感交流的缺席对彼此造成的创伤,使女儿学不会通过表达排遣负面情绪,只能采取放纵情欲的极端方式,用自毁来自我疏解。郭家的几回争吵中,男性成员普遍选择逃避——父亲拂袖而去、哥哥不辞而别——来搁置冲突,而文玥看起来“脾气火爆”,却对当下的感受极其忠诚。她的言行皆基于感性,但同时也勇于为感性的那一面负责,在照护瘫痪的文哥时,她看上去喜怒无常,对父亲的顽固不化而不解,也为父亲的行动不便而心疼,更是在父亲的一次次回避后仍然不懈地追问他对自己的看法,既耐心又任性。这些斑斓的情感变化,恰恰证明了父女关系不止于责任,而是仍含有两颗心的在场、两具身体的互相触动。如果说“抚慰生者”是丧葬师的终极目标,那么它也是郭文玥再稀松不过的日常,最终令文哥在爱而非沉默和忍受中安然离去,找寻到真正的宁静。

《破·地狱》剧照
哀悼之必要性在于人们能从中提取出一股普遍性的力量,它引起的悲伤不仅面向自我,也指向了他人和更广阔的社会关联。在最后的破地狱仪式中,无论是红衣起舞的郭文玥,安然离世的Hello文,还是主持仪式的见证人道生,他们都从明镜一般熊熊燃烧的火焰中获得了于自己人生有益的洞见,既感到生之有限,又进一步确信了爱之紧迫。电影揭开这世界最为神秘的面纱一角,它的成功似乎也在证实,死亡带来的教义兴许不只是摧毁,相反,它启发人去感受周遭活生生的器官运作的声音,从而致力于维护生命间“柔情的共同生活”。对于尸体的大胆暴露,也呵退了由于未知造成的恐惧,把病变和衰败变成了一件真正“亲切”的事,这就像巴特在母亲离世的漩涡中挣扎着写下的:“不,丧伤(忧郁)不是一种病。既非病,他们指望我如何治疗?回到什么状态?什么生活?服丧要努力的,应是通过它而重生,不再是一个平凡的人,而是一个更道德、更有价值的人,不仅是服了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