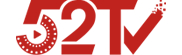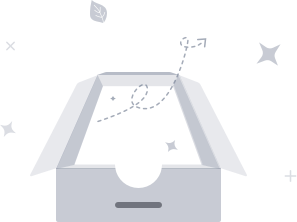大女主戏失灵,怪不了赵丽颖

主打女性救赎故事的《向阳·花》,从预告片播出开始,就博得了不少观众的好感和关注。然而,虽然顶着冯小刚的名导光环、赵丽颖积累的观众缘,以及全女性阵容的口号,该片在上映后还是遭遇了口碑滑铁卢,豆瓣评分6.6。
有人不解,为底层女性群体发声,强调她们的不服输精神,反社会歧视、反性暴力,冯小刚明明已经很“努力”拍女性了,问题到底出在哪?
(图/《向阳·花》)
从题材而言,冯小刚确实做到了努力。《向阳·花》改编自作家虫安的《教改往事》的其中一个短篇,小说聚焦女子监狱的众生百态,是一本非虚构纪实的狱警手记。
电影里的故事,则有意改编成女性群像的故事。
赵丽颖扮演的“白狐狸”先是为了帮弟弟娶媳妇,“换亲”嫁给瘸腿丈夫,后是生下失聪的女儿,为了攒20万人工耳蜗的手术费,冒险当擦边主播,最终锒铛入狱。狱中,她遇到了在盗窃集团长大的女小偷、谎话连篇的“毒友”,这些女人聚在一起,谈论过往的人生,她们曾因所处之境选择匮乏而“变坏”,又因自强不息而悬崖勒马。
(图/《向阳·花》)
女监里的“向阳花”要开出高墙外,底层女性互助、努力求生的故事当然很值得在大银幕上多多呈现,但对于《向阳·花》的诸多情节,观众显然没有完全买账。虽然人物的灵感源于非虚构文本,人物的细节和逻辑却无法构建起真实的基底。
有人质疑电影的剧本是在“消费苦难”,女性之间的争吵、和好也完全“没有逻辑”。实际上,电影更本质的问题是性别叙事的混乱,让人难以相信且进入故事:《向阳·花》拍的是女性,演的却是“老炮儿”的情节。
男导演与女性故事的错位
算上《我不是潘金莲》《芳华》《回响》,这已经是冯小刚第四次拍以女性为主要人物的作品了。老牌商业大导演的嗅觉是灵敏的,在女性电影的蓝海下,多少男导演扎堆开拍女子故事,然而市场大,却不意味着赛道好闯,作品好不好,终归还得过观众那关。
陈思诚监制的《消失的她》《默杀》一度获得了热度和票房上的成功,但情节与镜头颇受争议,比如女性被杀害、被侵犯的情节,让部分观众表示难以适应,质疑电影把女性苦难当作奇观。当男导演拍女性片,经常难以掩饰自己不自觉的男性凝视:当他们展示这些痛苦的镜头,到底把女性当作某种臆想和想象的对象,还是努力真实地呈现女性?
能将女性故事拍得好的男导演不是没有。30多年前,关锦鹏拍的《阮玲玉》就是很好的作品。阮玲玉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影星,短短的25年光阴,她经历了人生的崛起、复杂轰动的恋情,又服下安眠药离世。她的生活在八卦镁光灯之下,命运多舛,但电影并没有把猎奇的目光投向她,而是挖掘她内心的苦闷与挣扎。

(图/《阮玲玉》)
冯小刚的电影一直有人文关怀的影子。早年的他自称“市民导演”,他关注观众的需求,也很懂得如何取悦观众。
1997年的《甲方乙方》,是借用自由职业者开办“好梦一日游”业务的故事,对人内心的欲望进行了调侃。
2000年后,冯小刚执导的《手机》《天下无贼》《非诚勿扰》,不仅题材紧跟社会话题,作品也都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但这样一位大导演,却一次又一次死磕女性故事。从2023年的网剧《回响》到《向阳·花》,冯小刚的表达与观众的观感错位,观众对这些作品的不满和质疑,本质上是认为冯小刚对女性的理解仍然有些陈旧。女性不是隐忍、柔弱、妩媚的代名词,但女性气质也和男性气质或者“男性气概”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图/《向阳·花》)
《向阳·花》首先在女性友谊、女性江湖的呈现上有所偏差。如果抛开《向阳·花》中的女性阵容,这几乎就是《老炮儿》的翻版。《向阳·花》里,白狐狸有一位好友,叫黑妹。黑妹从小生活在盗窃集团,是小偷。两人被放出后,找不到工作,于是合伙搞起了卖门锁的生意。然而,观点不同的她俩合作不融洽,这两人开始互相指责、掀桌对骂。许多观众不理解为什么要融入那么多的“暴力情节”,不管戏中白狐狸和黑妹的冲突,还是狱中的互殴、与老板的对垒、和朋友的不打不相识,似乎都仍然如男性叙事一样,以肉体碰撞作为相互认知的途径,难道底层女性困境只能这样呈现吗?冯小刚忽视了一个事实,在泥沼中打滚的女性,相比肉体,智力与对人性的理解,通常是她们更有力的武器。
但对于冯小刚而言,这或许只是一种性别观念上的错位,因为在他的认知里,江湖就是这样的,男性友谊是靠拳头换取认可的,话语权也是靠拳头争取来的。
当老炮儿遇上大女主
2015年,冯小刚监制《老炮儿》,并出演其中的“六爷”一角。六爷是个北京老炮儿,在北京方言里,老炮儿原指“无所事事的老混混”,后来被用以形容在江湖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前辈。他们有自己的原则,遵从道上的规矩,用拳头在四九城呼啸而过,是他们的青春、文化和信仰。如果谈判时道理讲不通,就用老江湖的方法来解决。六爷说:“打架也是江湖”。

(图/《老炮儿》)
冯小刚或许某种程度上认可电影所阐述的江湖规则。于是,当要拍摄底层女性如何混江湖、如何在江湖中打出一片天的时候,他也自然而然地把那种传统的男性抢江湖、招揽铁哥们的方式,运用在了《向阳·花》里。除了不打不相识的情节,还有结尾处几个姑娘端起香,朝着关公结拜与表态“我不惹事也不怕事”的一幕,这些都是传统电影中惯常用来塑造男性江湖的桥段。

(图/《向阳·花》)
但观众很难想象,为什么一部主打女性故事的电影,看起来却有浓重的“老炮儿”气质。无论干架、掀桌、结拜,女性用这样的方式去强调自己的存在,本质上,其实都源于男性气概对“强”的理解偏差。保有女性自身的特质是不是就代表了不够强?打不过是不是就不够强?如果唯有去性别化才能获得力量、才能在江湖中站稳脚跟,那它依然是以男性叙事逻辑为主的电影。
江湖是男性的江湖,也有无数属于女性的江湖。要谈女性捍卫话语权,《风吹半夏》早就有好答案。同样是讲底层女性的摸爬滚打,但许半夏的逻辑完全不同。面对一圈心怀鬼胎的男人和狡诈的杯觥交错,她既不试图掩盖女性的弱势,也不傻傻地模仿另一性,而是笑嘻嘻地借力发挥,察言观色,在周旋间顺风而行。

(图/《风吹半夏》)
她偶尔柔弱、彷徨,但被占了便宜,事后一定要把局面扳回来。商战也是一种江湖,许半夏的存在告诉观众,原来女性混江湖,是可以不需要完全模仿男人、是可以游刃有余的。故事也展示了一个女商人的困境:当她是一位女性,哪怕本领再大,仍然会因为性别本身而遭遇不合理的蔑视。她需要找到自己的路径,再去击碎不合理的规则。
讲普通人,抹去复杂就没味道了
从早期开始,冯小刚的题材就在关注普通人。《天下无贼》讲的是一个贼遇到农民工后觉悟的良心,《手机》则反思了新千年的技术发展,如何给人带来了信任危机。在《向阳·花》的采访中,冯小刚也表达了他对底层特殊女性的关怀,他觉得这样一群女性聚在一起“应该是有希望的”。

(图/《向阳·花》)
但在情怀之外,冯小刚的笔墨始终充满着戏剧的技巧,比如,靠冲突推动的情节,还有近乎“完美”人设——白狐狸太“完美”了,这种完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白花”,而是一个缺乏复杂度的“完美受害者”,与白狐狸的经历难以契合。
冯小刚早期电影好看,除了题材的挖掘和导演本身的思考,还因为叙事的技巧。他会为观众精心设计各种有趣的桥段,巧妙地“节外生枝”,让观众产生心情跌宕起伏的观感。譬如《不见不散》中刘元与李清的爱情故事,他们每次见面都会碰到倒霉的事,为了追求李清,葛优扮演的刘元还假装成盲人与她见面,当骗局被撕破,他又锲而不舍地布局“捉弄”。

(图/《不见不散》)
在《向阳·花》中,这样的技巧同样比比皆是。王菊扮演的狱友组长胡萍,从与白狐狸敌对,到仗义相助,携手搞好洗车厂,中间不过是衔接了一段白狐狸送钱给胡萍爷爷奶奶500元的戏份。这样的情节固然能通过化敌为友的剧情展现女性群像戏的互帮互助,但人物弧光的转折来得实在过于突然,观众还没来得及深入细细品味两人的友谊,人物已经完成了她的工具性任务。
冯小刚进军女性故事赛道的决心和努力,是好事。他的进步,背后其实也印证了一个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女性故事了。但经过这么几年的产出,女性电影其实已经来到了全新的阶段。前有邵艺辉的《好东西》,后有《还有明天》《初步举证》的上映,这些作品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现女性的生活,更深层次地挖掘她们的思考。如果男导演只是单纯用讨巧的元素来呈现女性,用女性的故事去抢夺观众视线,而缺乏对她们深层的注视和理解,那么注定是很难过关的。